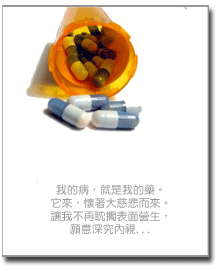说起自己学佛的经历,觉得很难下笔,因为劫难和头绪都很多,又怕有形文字,纠缠在世事之中,贻误他人,所以一直迟疑,不能落笔。佛子线上的斑竹再三邀约,我深知这是她的苦心,希望我自己曾经的挫折、辗转和感悟,能对大家有个参照。或许,我摔过跟斗,那个凸凹不平的地方我放块石板铺平,别人路过,就是坦途。如果真能这样,我愿意奉献自己的些微体会,与大家共勉分享。
一、
病来如山倒
如果说我现在与佛法的亲近,最早溯源,应该从疾病说起。
我的家庭是个多病多难之家。父亲和母亲都是遗腹子,他们生下来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。据说,爷爷是个茶商,多年来在山西和内蒙之间穿梭,26岁因为肺病客死异乡。奶奶守寡到38岁,得了咽喉癌,不能吞咽,生生饿死。这期间她的女儿,也就是我唯一的姑姑,因为难产而亡。所以,我的父亲,在16岁的时候,成了孤儿。
母亲还在姥姥腹中的时候,姥爷被阎锡山抓了壮丁。23岁战死沙场。姥姥21岁守寡,70岁去世。这其中49年间,行善茹素,唯一的心愿是求个好死,她是家里我见过的唯一老人。小的时候,常听她说一句,人活七十古来稀,我只求活到七十岁,跌倒就死,不拖累你们一个人。1983年,老人70周岁,无疾而终,在睡梦中与我们永别。
我5岁的时候,妹妹2岁。她和我的性格非常不同。我活泼好动,是个混世魔王。她优雅娴静,像妈妈。也许因为这个缘故,妈妈爱她尤甚。父母是从事核工业研究工作的,每逢一项大的核工程实验开始,他们都不能回家。我在那时,已经会做简单的饭食,懂得照顾妹妹。就是在那一年,妹妹因为误诊,患胸膜炎夭折。去的那一天,是父亲的生日。
我成了家里的独生女儿。却开始了与疾病的周旋。本身的体弱不足为谈。改变我整个理念的是12岁的那场大病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是10月2日,国庆日的第二天,是父亲的旧历生日。父亲自妹妹死后从不过生日,只有那一次,他因出差归来,与家人重逢,母亲说包顿饺子庆祝庆祝。于是,父亲一早起来,便洗床单洗衣服,又和好了肉馅,准备中午吃饺子。我在快开饭前,去了一个同学那里,去对作业的答案。当时,问过一句,你们家怎么还没吃饭?她告诉我说,因为她的妈妈住院了。我心中一凛。到现在,我也不知道,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,似乎受了暗示一般。回家的路上,我空腹吃了一个果丹皮,然后,上了四楼,进了家门,看见父母正系着围裙在包饺子,我伸手,眼前黑了下去。
从我们家到职工医院,路很远,父亲背着我,穿过山路,那情景历历在目,我完全知道,但我丝毫没有力气。至今我还能想起父亲疲累的喘息和我心疼抱愧的彼时心情。
到了医院,只有值班大夫,她们似乎都被我吓着了。我被推进抢救室,也不知为了什么。来了一个医生,她姓叶,是唯一镇定自若的人。她告诉我们,我是虚脱了。之后,便是上氧气。我睡了过去。
等我醒来,看见我的父母很可怜地坐在我床边。他们是那样地卑微无助。两个人都强打精神,看着我,有眼泪不敢流。接着,我开始反复。我告诉他们我的感觉,像有筷子顶在胃中,有呼没有吸,气不够用。我不断地换着姿势,或躺卧或坐起,一刻不能停歇。我的至亲父母一点忙都帮不上。大夫又来,疑惑地给我输氧。从那一天起,我忽而被诊断为心脏病,忽而又说我贫血,也有说青春期综合症云云。不管说是什么病,七天来一直用的是一种药。父亲害怕了,害怕剩下的这个孩子再次被单位的医院耽误,于是星夜兼程,从基地赶往成都。
入住四川省人民医院后,我更是经历了终生难忘的事情。在我住的那个病房里,有两个孩子是白血病。父母到了成都的第一天,就给我买了很多的东西。母亲生性节俭,很少给我添置新衣。那天,他们来探视我,除了新衣新鞋,妈妈甚至给我买了一根镀金的项链!我当时想,也许,我要死了吧。他们这样安慰我?
我的病,一直确诊不了,不断地血检尿检已经派不上用场了,大夫说只有骨穿了。骨穿,是通过穿刺骨髓,并且提取骨髓来化验的一种方法。4个川医大的实习生摁住我,一个女实习生来穿刺,我大哭不止,哭声穿越了整个住院大楼,一直到一楼的锅炉房,母亲因为无法面对,躲在那里打水,结果开水烫伤了手臂。我同屋的小病友纷纷来到我的床前,他们以久病之身,鼓励我的意志。
深夜来临,我在自己的病中辗转反侧,不能安眠。我甚至不敢想到呼吸,我一想到它,就怕它因为我的注意而变得急促,急促到窒息。但我又不能不注意它,于是,我经常摁响急救铃,值班的大夫护士因为我的恐惧不知道白跑了多少趟。后来,我不敢麻烦他们,开始自己面对不能放弃的执着——呼吸。我想,再没有人可以帮你啦!爸爸妈妈夜里不能陪床,医生护士不能总是被我虚惊,只有自己。最害怕的时候,只有自己。
也许是因为累了,我昏昏睡去。
之后,我开始不停地上厕所。我一紧张就想去。很不幸,我总是紧张,于是我总去。我不敢把自己害怕的东西告诉别人,我只有独自担当。
接着,我的病友死了。
妈妈告诉我那两个孩子是先天的造血功能障碍。没办法的。
我久久地沉默。
我们家鲜有老人,少有眷顾。尘世间的金钱、权力、地位和荣誉都不在我们的生活范畴。我是个笨孩子。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。学东西很慢。自行车学了將近三年才会骑。学习也不好。出类拔萃跟我长期形同陌路。病痛、羸弱和死亡,在我幼年时代就如此深重,它让我不再是个贪恋遊戏的孩子,不再在学校、玩伴当中正常过活。
我自己有病,有一些病痛的秘密,不能言说,无法解决。
我的病在没有确诊下自行痊癒,在很多时候,我只是在医院住着。不吃药,不打针,不去上学。只是住着。看着病,看着生死离别。
从医院回到学校以后,我整个人发生了巨变。蝇头快活已经不再能够让我动心停留。疾病,如山一般的疾病;还有恐惧,孤独面对的恐惧;别离,别离之后的去向。。。。。。这些,都成为我生命的悬疑,等待揭密,等待愚癡的心灵被开启。
85年,我们全家举家北迁,回到家乡太原。我曾经又犯过一次病。一模一样的感觉。一个中医来看我。一针紮在胃上。说,这是胃涨。进了凉气。从此,病不再犯。
多年以后,我含着泪光遥望我的疾患,仿佛看到那个天佑的赤子,在懵懂惶恐的少年时代,经历的无边苦海变做了殷殷福田。我的病,就是我的药。它来,怀着大慈悲而来。让我不再耽搁表面营生,愿意深究内视。这真真应了那句老话:磨难,就是财富。佛祖不是也说吗,烦恼,即是菩提啊!
《下期待续》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