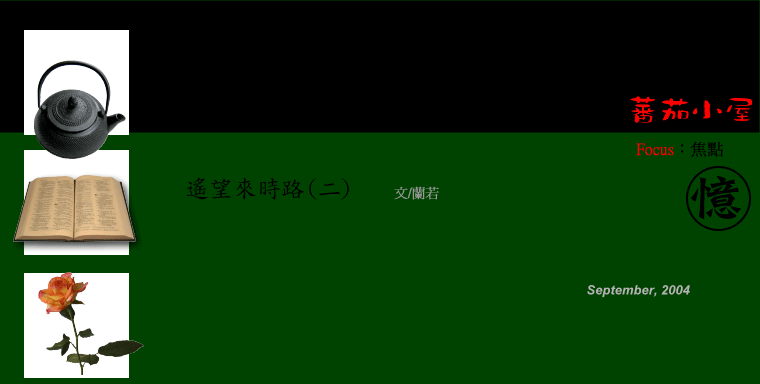|
我无路可去。我的嫂娘——大表哥的岳母告诉我,孩子,别闷在家里,去五台山玩吧!
由此,我的人生发生了真正的改变。
我经嫂娘介绍,来到普壽寺。这是五台山继集福寺之后的第二座尼众寺庙。开创者是当代南山律宗师弘一法师的师弟通愿法师。通老有两个弟子,如瑞和妙音。我去的那年,如瑞在做教务长,妙音是律学院的当家师。而如瑞师父是嫂娘的外甥女,因了这一层,我得住客房。
在此之前,我曾经来过五台。不过那是作为遊客,跟父亲一起来玩。我到了普壽寺后,如师父问我,想怎样度过假期?我不假思索地说:师父,我并非度假,我是要学佛的。一语落地,师父微笑不答:现在五台,正是最美季节,你可以到处看看么。我断然拒绝,说,我要跟小师父们一起学佛。师父再笑,起身离座去了。
接下来的三个月,我有幸得瞻修律的比丘尼们那日日夜夜的苦行。
晨3:00起,上早课;5:00下课,或劳动或自习,各行其是;上午8:00,有师父授课;过午不食;下午或拜忏或静坐;夜10:00眠。平日里沈默端肃,温和敦厚。吃饭的时候,必先唱经,领唱师唱罢,必来到佛堂之角,给饿鬼冤亲施当日食。每人面前一钵一碗,一一落座之后,有值班的小师父来为大家盛饭盛菜,她举着饭勺殷切看你,你用筷子在碗边沿划线,你能吃多少,就划到多少。若没吃饱,可以看向小师父,她必留意你,再来给你添饭。。。此前,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苦行,从未看到过他们在海青芒鞋下的金刚之心。我目睹耳闻,终日里望着客堂的那幅“以戒为师”发呆。那个时候,嫂娘的姐姐已经出家多年,她曾经带着我翻过三座山,往深山里的寺庙送粮送菜,我不觉苦,亦不觉累,脚力深厚,心中欢喜莫名。我愿意,为师父们做这些。如果,我还能做这些的话。
日子很快过去了。一天,妈妈打来电话,说电影学院有个干部进修班,班主任是我们的主考老师之一,她问母亲我的下落,希望我能继续考一次。我非常动摇。来到客堂,不敢看如师父。师父正在和几个居士说话。良久,他唤我说,明天你下山去吧。不要让你妈妈担心。我小声说,师父,我愿意留下的。如师父洞察我心,他又微笑,下山去,好好努力,不要抱怨,管好自己。夜深了,我听见五台的溪流潺潺作响,窗櫺之外,有月朗照,终夜不能入眠。

第二天,我要上路了。那时侯,五台到太原的汽车经常在路上遭遇车匪路霸,我来时因为搭父母单位的旅遊车,去时却只能坐这种公车了。如师父慈悲,送我亲手做的普壽寺的寶葫芦,挂在我的胸前,她告诉我说,管好自己,有护法跟着你呢,不怕!
于是,我上路。
路上,果然有恶徒上车,我一路垂目念佛,平安度过。
第四年,我来到北京,我的老师告诉我,虽有隐情,但我要学会忍辱。希望我能坚持。于是,一年之中,我心无旁骛,不求命运转机,不怪责他人,不计较得失。日子倏忽而过。
7月未来,我已经收到了三所院校的文考通知单,8月,我以专业文化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被电影学院录取。通知书下来后,父母抱头痛哭。而我,已然无泪。我真正的大学生活已经在录取之前艰难度过了。
管好自己。这是如师父一再告诫我的话。观照我的考学经历,每一次犯的错,我不是不知道,但我就是不能不放逸,任由自己心猿意马,不能专心。结果,吃苦受累的只有自己。没有什么外物可以为我的苦难负责。唯一要负责的人是我自己。而这个时候,所谓苦难,已经不再是值得称道的东西,它是我不能端正本心的印记。甚至,我也不能和任何人攀比,攀比不同业力所造成的果报,是太大的妄想。我能做的,就是改变自己。清淨这颗怀有太多梦想和妄想的心灵!
图:「天心月圆」音乐剧剧照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