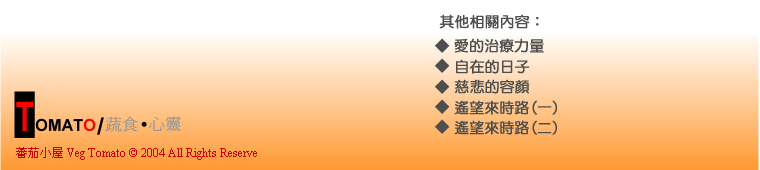|
进入大学校门之后,如你所料,我最先遭遇的不是学业,是爱情。
在爱情面前,我完全是个沉睡不起的人。也许是因为自闭甚久,自视又甚高,自以为曾经沧海,所以很难在尘世的感情当中翻浪动心。我碰到过一些男孩子,他们对我很好,有着这样那样的优点,但是,我却没有足够的耐心,为他们而停留。我仿佛患有精神洁癖,总能看到他们身上让我失望的那一面,那瑕疵让我毫不犹豫地將一切牵绊弃绝。然而,我看到他们伤心,心里又非常自责。常常为此扪心自问,是否因为自己的决绝,给别人造成了伤害?
那是我不愿看到的。我的本意不是伤害。我因此莫衷于是。长久地关闭着心门。
直到我看到师兄明亮。
师兄学佛,深入经藏,以淨空法师一句“老实念佛”为法门,劝诫同修道友放下轻狂,笃实学佛。他们班中有个旁听生,唤做蓬斗,大家觉得他是混混,都敬而远之。只有明亮,悉心以待,毫不讥嫌。蓬斗是北方人,喜欢吃面食,每次吃馒头的时候,都把馒头皮扔掉,大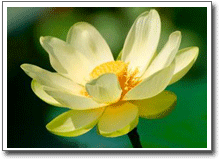 家都觉得浪费,纷纷指责。蓬斗却依然故我,屡教不改。明亮师兄不落一句苛责,捡起蓬斗扔掉的馒头皮,当众咽下。蓬斗深受震动,从此恶习不犯。 家都觉得浪费,纷纷指责。蓬斗却依然故我,屡教不改。明亮师兄不落一句苛责,捡起蓬斗扔掉的馒头皮,当众咽下。蓬斗深受震动,从此恶习不犯。
我认识师兄十几年来,他不纷扰,不攀缘,不诳语,安静守己,沈默自尊,身边的朋友因他而纷纷学佛。
我因同道而生知己之心,因景仰而萌眷爱之意,因其威仪而愿跟随,因其洞察而着相守。为了他,多年来我写下了大量劄记,于瞬间理解了所有渴爱的诗篇。我默守着思念,按捺住如鹿撞般的心灵,不敢言爱,怕扰道心。
记得早在上学之初,我曾写过一个短剧,叫做《末法时代》。我拿了自己勤工俭学的钱找同学一起来拍摄。大家看了剧本纷纷摇头,表示不懂。一个同学说,你可以找明亮师兄来演,他是佛子,应该明白。这是初闻兄名的机缘。
明亮看完剧本之后对我说,兰若,你知道,有时候,我们的理解会耽误别人。我害怕他拒绝,便说,如果没有人做佛教的宣传,知道的人不是更少吗?师兄说,你打算用这部片子宣传佛教吗?我低头,不能回答。他又说,如果你只是作为自己拍摄的作业,想练习技巧,你可以拍。但是,如果你要作他用,我觉得可能不妥。
这次谈话,我备受打击。师兄的意思是我尚在迷中,怎能以迷唤迷,更加贻误他人?
8月夜,空荡荡的学生公寓,倾盆的雨。师兄骑了自行车,穿越了大半个北京城,从剧组回来找我,他抹去脸上的雨水,递给我剧本说,我写了些意见,你参考着看。这个我可能演不了,但是我推荐一个人,他比我更合适。
师兄又匆匆离去。看着他雨中奔劳的背影,我无言以对。
拍摄开始了。工作比我想像的要复杂艰深得多。摄影总是在问我,机器架在哪儿?这儿你分几个镜头?你打算怎么剪?能接得上吗?说老实话,我听见他连珠炮的问题,屡次要昏倒在地——刚开始学电影,我哪儿懂得技巧啊!!这时,师兄总能抽了空,带了他的朋友来,有时候换场景,有时候搬东西,他常常沈默地看着我们,在我完工之前悄然离去,让我不及言谢,便影踪杳杳。
我的片子终于拍砸了。看着一大堆素材,我无从下手。录音师开玩笑,讲他们私下里说我是个化神奇为腐朽的“大师”,写的拍的不仅旁人不懂,自己也晕菜。我听后,汗颜不已。这时候,想起明亮师兄的初衷和沈默。我惭愧万分。
此剧之后,我开始努力,再不敢不懂装懂,似是而非。于佛,更加不敢言诠。
我默默地写诗,悄然谛听深夜里有花坠落的声音,我去看所有师兄出演的剧目,拍烂了巴掌,羞红了脸,所有你们在爱的时候干过的傻事,我一样都没拉下。我看到曹禺剧目《北京人》里的愫芳说,我爱他,便爱他曾经珍爱过的一切。呜呼,我亦不能倖免。我从画报上剪下他的照片,放到本中。又怕遗失,放在像框的背后。怕别人发现,又屡次转移。最终不知所终。后来,我翻开画报,看见那一页上徒留了文字,感慨如果我不执着,那照片还在,如今,却了不可得!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