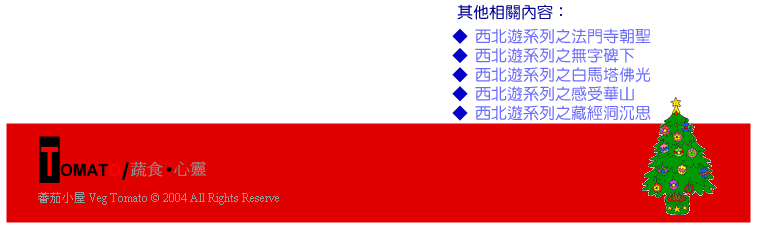西北游——夜行柳园
大漠夜行,为我的人生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和体验。
记得从鸣沙山回到敦煌,已是夜里十点,约好返回嘉峪关的计程车因故不能启程,深夜11点,我们另租了一辆车赶往柳园火车站。
广袤的大漠上,只有我们的车在宽阔的马路上孤独地奔驰着。疲惫的我,在女儿一声声地惊呼中无力地抬起头来,顺着女儿的视线,我看到了那灿若明珠的星空,刹时间精神振奋,睡意全消。我默默地凝视着车外闪烁的星空,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。那澄澈的天空,那璀璨的星河,离我们那么近,那么近,似乎伸手可触。坐在疾驶的车上,仿佛在看一部环幕立体电影,身边的一切那么逼真,又那么虚幻。渐渐地,自己也好象溶入了虚空,与天地成为一体。
星空下,白日荒芜寂静的大漠变得生机勃勃,草丛中潜伏的燥动,路两旁忙碌的奔波,昭示着无处不在的生命活力。车前常有小动物横越公路,与飞驰的汽车抢道,它们顽皮如同懵懂小儿,不知危险就在眼前,我的心常常随着女儿一惊一咋的叫声突突地上下乱窜。几只兔子和跳鼠几乎是与汽车擦肩而过,而笨拙的刺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司机说,前几年一趟车跑下来,撞死几只野兔、刺猬是常事,近年来,小动物比以前灵了,数量也没有那么多,故免费野味也就少了。说话间,只见一刺猬躲避不及,擦过车轮,我们赶紧下车查看,果然见一只可怜的小刺猬惨死路旁。摸摸它的小胸脯还温热轻软,心中十分不忍,嘱司机减速慢开。
司机又打开话匣子,说如果不是赶时间,便可凭藉一把手电筒,在一丛丛的马棘草中活抓刺猬。刺猬自我保护的本领是一遇上危险,便竖起全身又硬又粗的刺,缩起头来,一动不动。这一招对付其他动物还顶用,对人就等于是束手就擒。但大漠的夏夜,蚊猛袭人,常常是抓一只刺猬,被恶蚊叮几个大疙瘩。我想,这也许是上苍对强者的一个警示性的惩罚吧。接着,他又介绍如何將刺猬变成盘中餐,肚中物,那过程实在很残忍,也只有别出心裁,自认为强大聪明的人才能想得出来。
司机是个刚做了父亲的年轻人,在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中,他一直很健谈,也很坦诚。说起才几个月大的女儿,他的语调多了几分柔情,他说之所以如此辛勤,是为了妻子和女儿,他毫不掩饰他为人夫、为人父的快乐和骄傲,很自豪能担负起这份家庭责任。他说几年前还是个打家劫舍,闹得四邻不安的混小子,翘课、斗殴、偷盗,无恶不作,局子里几进几出,直到把身为中学校长的父亲活活气死,他坦言今天的改变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。我说:“代价未免太大了。”
“是啊!从前我嫌他啰嗦、老套,现在,我真的很想再听听他的教导,但永远也听不到了。”他的声音变得沉重起来。
“后悔吗?”我问。
“很后悔。”他伤心地说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好残酷,于是宽慰他道:“你后悔了,改过了,这就是对父亲的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。”
他告诉我们父亲生前很希望他能读大学,可是初中毕业他就缀学了。
“成绩不好吗?”我问。
“成绩很好。”
“那为什么不继续读下去呢?”
“我认为自己太聪明了,老师都没水平教我了。于是,我就翘课了......与一帮坏小子盡干一些偷鸡摸狗、扰乱四邻的坏事。”
他还说很想读书,但已没有机会了,现在自己做了父亲,才深深体会到父亲当时的心情。
我望着满天繁星,有一种莫名的感动,为明澈的夜空,为复苏的人性,也为那唤醒人类善美本质的亲情。
富于幻想的女儿曾在一篇作文中写道:“只要洗淨了心灵的尘埃,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在天上的位置,都会更清晰地看清自己——天空中那颗属于自己的小星星。”此刻,我才深悟到孩子的心灵世界是那么清纯,那么完美,那么接近真理。
我唯愿將这星夜的一切留在记忆里,因为它们那么美,那么真......
午夜一点半,我们抵达柳园火车站。司机说他会在车上小憩一会儿,运气好的话,说不定能载客返回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