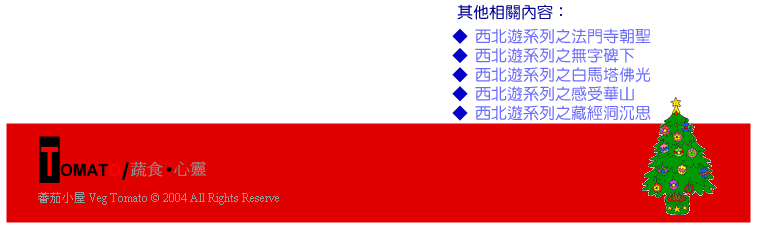西北游——夜行柳園
大漠夜行,為我的人生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憶和體驗。
記得從鳴沙山回到敦煌,已是夜裏十點,約好返回嘉峪關的計程車因故不能啟程,深夜11點,我們另租了一輛車趕往柳園火車站。
廣袤的大漠上,只有我們的車在寬闊的馬路上孤獨地奔馳著。疲憊的我,在女兒一聲聲地驚呼中無力地抬起頭來,順著女兒的視線,我看到了那燦若明珠的星空,剎時間精神振奮,睡意全消。我默默地凝視著車外閃爍的星空,有一種久違了的感覺。那澄澈的天空,那璀璨的星河,離我們那麼近,那麼近,似乎伸手可觸。坐在疾駛的車上,仿佛在看一部環幕立體電影,身邊的一切那麼逼真,又那麼虛幻。漸漸地,自己也好象溶入了虛空,與天地成為一體。
星空下,白日荒蕪寂靜的大漠變得生機勃勃,草叢中潛伏的燥動,路兩旁忙碌的奔波,昭示著無處不在的生命活力。車前常有小動物橫越公路,與飛馳的汽車搶道,它們頑皮如同懵懂小兒,不知危險就在眼前,我的心常常隨著女兒一驚一咋的叫聲突突地上下亂竄。幾隻兔子和跳鼠幾乎是與汽車擦肩而過,而笨拙的刺蝟就沒有那麼幸運了。司機說,前幾年一趟車跑下來,撞死幾隻野兔、刺蝟是常事,近年來,小動物比以前靈了,數量也沒有那麼多,故免費野味也就少了。說話間,只見一刺蝟躲避不及,擦過車輪,我們趕緊下車查看,果然見一隻可憐的小刺蝟慘死路旁。摸摸它的小胸脯還溫熱輕軟,心中十分不忍,囑司機減速慢開。
司機又打開話匣子,說如果不是趕時間,便可憑藉一把手電筒,在一叢叢的馬棘草中活抓刺蝟。刺蝟自我保護的本領是一遇上危險,便豎起全身又硬又粗的刺,縮起頭來,一動不動。這一招對付其他動物還頂用,對人就等於是束手就擒。但大漠的夏夜,蚊猛襲人,常常是抓一隻刺蝟,被惡蚊叮幾個大疙瘩。我想,這也許是上蒼對強者的一個警示性的懲罰吧。接著,他又介紹如何將刺蝟變成盤中餐,肚中物,那過程實在很殘忍,也只有別出心裁,自認為強大聰明的人才能想得出來。
司機是個剛做了父親的年輕人,在兩個多小時的車程中,他一直很健談,也很坦誠。說起才幾個月大的女兒,他的語調多了幾分柔情,他說之所以如此辛勤,是為了妻子和女兒,他毫不掩飾他為人夫、為人父的快樂和驕傲,很自豪能擔負起這份家庭責任。他說幾年前還是個打家劫舍,鬧得四鄰不安的混小子,翹課、鬥毆、偷盜,無惡不作,局子裏幾進幾出,直到把身為中學校長的父親活活氣死,他坦言今天的改變是父親用生命換來的。我說:“代價未免太大了。”
“是啊!從前我嫌他囉嗦、老套,現在,我真的很想再聽聽他的教導,但永遠也聽不到了。”他的聲音變得沉重起來。
“後悔嗎?”我問。
“很後悔。”他傷心地說。我突然覺得自己好殘酷,於是寬慰他道:“你後悔了,改過了,這就是對父親的在天之靈最好的告慰。”
他告訴我們父親生前很希望他能讀大學,可是初中畢業他就綴學了。
“成績不好嗎?”我問。
“成績很好。”
“那為什麼不繼續讀下去呢?”
“我認為自己太聰明了,老師都沒水平教我了。於是,我就翹課了......與一幫壞小子盡幹一些偷雞摸狗、擾亂四鄰的壞事。”
他還說很想讀書,但已沒有機會了,現在自己做了父親,才深深體會到父親當時的心情。
我望著滿天繁星,有一種莫名的感動,為明澈的夜空,為復蘇的人性,也為那喚醒人類善美本質的親情。
富於幻想的女兒曾在一篇作文中寫道:“只要洗淨了心靈的塵埃,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在天上的位置,都會更清晰地看清自己——天空中那顆屬於自己的小星星。”此刻,我才深悟到孩子的心靈世界是那麼清純,那麼完美,那麼接近真理。
我唯願將這星夜的一切留在記憶裏,因為它們那麼美,那麼真......
午夜一點半,我們抵達柳園火車站。司機說他會在車上小憩一會兒,運氣好的話,說不定能載客返回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