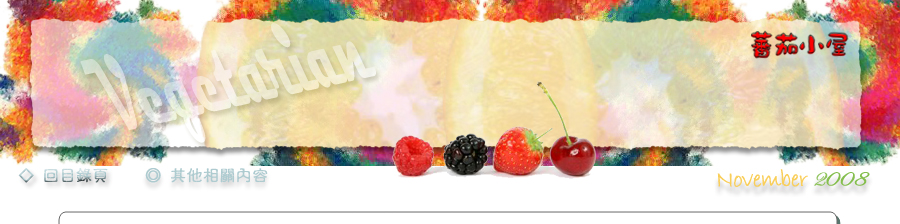|
每次見到司徒的時候他都有兩個特徵,一是相機不離身,再來就是臉上總帶著微笑。位於澳洲雪梨的南天寺,屬於漢傳的佛教寺院,僧眾及信徒多為亞裔,舉辦的法會活動也都使用中文。司徒在咨詢室(information
desk)做義工,他是荷蘭人。雖然不懂中文,但卻完全沒有影響他的工作,反而因為語言及背景的差異,和周遭的人擦出另類的火花。
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超越語言界限的。」第一次見面時司徒這樣和我說,「佛法也是。中文也好,英文也好,荷蘭文也好,語言只是一個工具,讓人們瞭解真理的工具,當我們真正體解了真義,達到了認識,那麼運用哪種語言,甚至是否需要運用語言,都無關緊要了。」
「就好比微笑是全世界都通用的問候一樣。」我點頭。
「當然,如果你和我講中文,我和你講荷蘭文,到最後我們或許會有共識,但遠遠不及我們一起用英文溝通來的有效率。」他哈哈笑了幾聲,「所以雖說語言不重要,但也不能說語言毫無用途。」
多日後,我誦讀金剛經時,
忽然想到司徒的這番話,感嘆著他已經把般若智慧融入生活,並成功地證實給了身邊的人。
司徒退休前是警察,閱人無數,也經歷了許多常人無法想象的歷練,所以對事物的看法會有獨到的見解。他認為人生的意義就是分享和奉獻。司徒酷愛旅行,更喜歡用相機記錄生命。他把退休後的重心一半撥分在背相機,一半撥分在當義工。來到南天寺,正好讓他有機會把兩者合為一體。這些年來南天寺重要的法會,都經由他的鏡頭,拍攝下許多寶貴的記錄。
司徒有著圓圓的啤酒肚。遠遠地,只要看到一個超大單眼相機鏡頭掛在圓滾滾的身前,並聽到爽朗的笑聲,大家都知道那是司徒。有位法師某天笑著稱他為【Happy
Buddha】,眾人才恍然覺得他真的與滿臉笑容的彌勒佛有幾分神似,於是南天寺各分院的義工朋友們都喚他Happy
Buddha,司徒的笑聲穿透力也就更強了。
某天我不慎進食沾有海鮮的湯底,導致嚴重皮膚過敏,無數痕癢難忍的小紅疹,讓我坐立難安。當我捧著像蕃茄一樣腫起的臉頰唉聲嘆氣時,司徒給了我一個大笑臉。
「你應該高興才是。」他說,「這說明你是一名註定的素食者
(Vegetarian by Default), 而不是選擇性的素食者(
Vegetarian by Choice)。就好像我一樣。」
若是有選擇的,或許某天我會選擇捨棄素食這條路,而若是註定的,那麼素食這條我此生都會一直走下去。司徒的安慰讓我笑了。
「我對蜜蜂過敏。」司徒告訴我,「如果我被蜜蜂扎了,下一秒鐘我就封喉了。」
「這麼嚴重?」我驚訝。
「體質如此。」他對我擠擠眼,「我也是被菩薩挑選過,註定要成為素食者的呢!」
極度敏感的體質,局限著司徒的飲食選擇,除了不能進食肉食之外,連花生,牛奶,蚌殼類海鮮,
雞蛋,麥類 (wheat) , 酵素 (yeast),蜂蜜,咖啡因等等都是過敏原。他的過敏單很長一串,我越聽越心驚。
「巧克力也不能吃?」我睜大眼,「甚麼?麵粉也過敏?」
「一點也不影響我啊。」司徒摸摸自己的啤酒肚,「你看我照樣很開心,把自己養得圓滾圓滾的。」
司徒說過敏原好比戒律。很多人聽到「戒」就覺得自己是失去了自由,其實非然。有了戒,知道甚麼是被建議不要觸碰的,並付諸於行動,人生反而更廣闊。
「當我知道我不能喝牛奶,我就改喝豆漿。意識到牛奶是讓我上吐下瀉的原因,就停止去飲用,這樣我遠離病痛的折磨,難道不算是獲得了自由嗎?」司徒更深一層的嘗試解釋他的想法,「受戒也是如此,知道甚麼是讓自己身心不快樂的,就不要去毀犯,獲得的將會是更大的解脫。」
我很認同的。
不久前南天寺開設了佛學課程,法師以中文授課,我在課堂上很驚訝地看到司徒。
「你中文突飛猛進了啊?」我坐在了他身邊。
「我只是喜歡上課的環境,這裡的氣氛很鼓勵我。」他說,「看見這麼多年輕的佛學弟子,週末不是去逛街玩耍開派對,而是撥時間來這邊精進佛法,想到就讓我感動。」
但他遇見我了,我就是他的同聲翻譯。
我把法師在台上講的話即時打成英文顯示在筆記電腦上,他再把他的想法和回應打在他的電腦上。我們聽著法師的開示,並在同時展開著激烈的探討。一切都在無聲中進行,但互動是那麼的強烈。我在幾個瞬間有著深深的震撼,想起第一次見面時司徒說的那番話,語言只是一種形式,而很多東西,是超越形式,以無形的姿態存在著的。
司徒在韓國受五戒,日本受菩薩戒,曾在泰國住過非常久的一段時日。他有許多的機會接觸寺院,也和各道場,各宗派的僧眾結下深厚的因緣。當他展示歷年來在世界各國各寺院與各法師的合照時,我的眼中透露出羡慕的目光。
「我是幸運的。」司徒自己也承認,「我在寺院不僅認識了法師,並認識了許多年輕的義工,他們讓我的心永遠保持著青春活力,精進不懈。」
說完司徒把右手舉在空中,很鄭重地指了一下我,「好比妳,從妳身上我看到許多能量,所以不用對我說謝謝,妳也幫了我很多。」
我曾經不止一次抱怨,素肉素海鮮的腥味讓我感到陣陣不舒服,所以我都會特意挑出來,拜托身邊的朋友幫我吃掉。有天司徒喝完碗內最後一口湯,然後對我說,
「妳吃素,是因為身體不能接受肉味,對不對。」
我點頭。
「所以妳吃到素的肉,因為有肉味,所以感到不舒服,對不對。」
我再點頭。
「但妳如果告訴自己,那不是素魚,那只是香菇蒂;那不是肉味太濃,那只是菜味太淡;那不是假的肉,那其實是真的菜。妳心裡還會不舒服嗎?」
我歪了一下頭思考著。
「因為妳心中不停告訴自己,那是一塊有肉味的素食。一旦心裡堅持著這個想法,就開始把對肉的厭惡投射到這塊素菜上。於是吃在嘴裡,煩到心裡,越咀嚼越不舒服。」
我又點了一下頭。
 「嘗試著不去想,自己夾著的是假的肉塊,飄著的是真的肉香。不要起分辨心,不要起喜惡心,妳吃在嘴裡的只是一塊食物,是給妳這付色身皮囊的藥,讓進食後的妳,有力氣去學更多的知識,有精神去做更多的貢獻。不管是甚麼味道,喜歡或不喜歡,都讓自己去欣賞,而不是平白無故的給自己增添不必要的負擔。這樣妳打飯的時候不會罣礙碗中會不會有素肉,吃在嘴裡的時候也不會介意是不是有肉味,掙脫了自己給自己強加的所謂不吃素肉的框框,妳吃素的道路會走得更自在。」 「嘗試著不去想,自己夾著的是假的肉塊,飄著的是真的肉香。不要起分辨心,不要起喜惡心,妳吃在嘴裡的只是一塊食物,是給妳這付色身皮囊的藥,讓進食後的妳,有力氣去學更多的知識,有精神去做更多的貢獻。不管是甚麼味道,喜歡或不喜歡,都讓自己去欣賞,而不是平白無故的給自己增添不必要的負擔。這樣妳打飯的時候不會罣礙碗中會不會有素肉,吃在嘴裡的時候也不會介意是不是有肉味,掙脫了自己給自己強加的所謂不吃素肉的框框,妳吃素的道路會走得更自在。」
司徒的話讓我想了很久。到最後我忍不住還是寫了封信致謝。
「碗中有素肉就吃,沒素肉就不吃,遇到不喜歡的就包容,遇到喜歡的就感恩,很多事情,也就是這樣了。」我的感觸,一字一字地敲在鍵盤上。
「說過幾次了,不用謝我。」司徒回信的時候連打了好幾個哈哈哈。「我只是表達我的想法而已,真正在執行,在實踐,最後在受益的人,還是妳自己啊。」
三個月前的某天,司徒告訴我他會離開一陣子。
「我要去旅行了。」他這樣說,「先去新加坡,再去越南,韓國,日本,英國,西班牙,阿根廷,南極,還有好多我暫時想不起來的地方。」
「行程真豐富。」我嘆一聲。
「我快七十了,最近身體不好。」司徒說,「在還能四處逗留的時候,我想再去一次曾經感動過我的地方,和曾經感動過我的人好好說聲謝謝。」
我的眼中閃過一絲哀傷。
他立刻對我開懷大笑著,「妳別捨不得我啊!我會寄照片給妳的。」
陸陸續續地,我的信箱中出現著司徒的問候,顯示著各個城市不同IP。他用鏡頭捕捉著眼睛所想珍藏的片段,新加坡的車站,越南的河畔,柬普寨的浮雕,韓國的鐘樓,尼泊爾的夕陽,日本的寺院,阿根廷的極光。信中總是簡短報著平安,並告訴我相片的內容和故事的背景,卻從來不提他的下一站在哪裡,也不說會在哪個地方停留多久。司徒說充滿期待的人生,是最美好的。
我等著某天信箱中出現雪梨機場的照片,這樣我就知道,過不多久我就可以再見到他,總是帶著微笑的Happy
Buddha,健康平安的和我一起探討分享感觸感受。 |